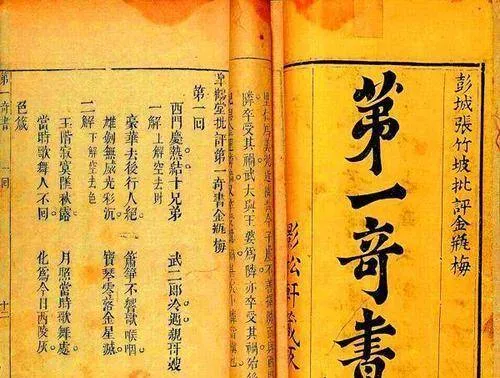《金瓶梅》其实是一部喜剧,其中有很多“天生的喜剧演员”
诸多富有戏剧性的人物形象是建构《金瓶梅》喜剧世界的重要基石之一。《金瓶梅》中的人物有很多都善于说笑嘲讽,幽默风趣,可谓天生的喜剧演员。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只是《金瓶梅》这部人生大戏的垫场角色,然其同样有着不输于几大主角的光彩照人的喜剧天赋。
首先,以玳安为首的诸多小厮所具备的喜剧特点值得注意。小厮是西门庆家中使用的奴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一行一动都与西门庆等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为了能够得到西门庆的赏识,在府邸之中获得立足之地,较为机敏的小厮大多机智幽默并善于随机应变,其中最具喜剧天分的就是最后承受西门庆家业的玳安。玳安懂得怎么做好奴才,也善于做这样的奴才。他能够摸透西门庆的好恶并据其眼色授意作出判断,乖巧圆滑地应对西门庆的身边人。他的喜剧性格独特之处就在于其赋予讽刺嘲笑这种喜剧表达方式以诙谐的寓意并借此迎合诸人,令人觉虽是在献媚讨好却并不因此而讨厌反感。在面对与西门庆关系密切的得宠者的时候,他会给予其并不尖刻的嘲笑及温和的打趣,令其言语对象感觉自己得到了关注,产生一种真假难辨的认同感,进而融入当时的喜剧语境之中。当然,玳安的喜剧性格只在西门庆认同并宠信的人物面前才会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为获得赏识,玳安这种独到的喜剧性格有时会在作为一家之主的西门庆面前主动表现。如第二十回,应伯爵等帮闲要拜见新嫁西门庆的李瓶儿,而西门庆并不愿早已熟识他们的瓶儿出见,然为众人逼迫不过,只得令玳安去向后说去。文中玳安回报的描写就颇能反映这一点:
半日,玳安出来回说:“六娘道,免了罢。”应伯爵道:“就是你这小狗骨秃儿的鬼,你几时往后边去,就来哄我!赌几个誓,真个我就后边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应二爹!二爹进去问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进去?左右花园中熟景,好不好我走进去,连你那几位娘都拉了出来。”玳安道:“俺家那大猱厮狗好不利害,倒没的把应二爹下半截撕下来。”伯爵故意下席,赶着玳安踢两脚,笑道:“好小狗骨秃儿,你伤的我好!趁早与我后边请去,请不将来,可二十栏杆。”把众人、四个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下边,又走来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动身。
玳安与伯爵这对喜剧高手既有动作又有对白的绘声绘色的表演,俨然就是一段短小精悍的即兴相声,博得了满堂彩。细究因由,玳安的所作所为是站在西门庆立场上对伯爵的取笑,恰恰迎合了与宴饮之时常以伯爵为篾片加以调侃的西门庆的心意,同时,又是斟酌主人深惧丢丑的心态,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对众人之行为的含蓄婉曲的劝阻。因此,玳安的此举表面上是对伯爵的毫无意义的耍弄,实则是对其主人西门庆的有意讨好。
玳安以调笑嬉戏为主的喜剧性格同样体现在西门庆不在场之时。在第二十三回的末尾有这样一处情节。宋惠莲得西门庆之幸,恃宠而骄。她在看中了花翠后,毫无顾忌地以西门庆所赠银子付账,此时玳安出现耍弄了她一番:
妇人向腰里摸出半侧银子儿来,……只见玳安走来,说道:“等我与嫂子凿。”一面接过银子在手,且不凿,只顾瞧那银子。妇人道:“贼猴儿,不凿,只情端详的是些什么?你半夜没听见狗咬?是偷来的银子。”玳安道:“偷倒不偷。这银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银子包儿里的。前日爹在灯市里,凿与买方金蛮子的银子,还剩了一半,就是这银子,我记得千真万真。”妇人道:“贼囚!一个天下人还有一样儿的。爹的银子,怎的到得我手里?”玳安笑道:“我知道什么帐儿。”妇人便赶着打。小厮把银子凿下七钱五分,交与买花翠的,把剩的银子拿在手里,不与他,去了。妇人道:“贼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汉。”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与我些儿买什么吃。”那妇人道:“贼猴儿,你递过来,我与你。”哄的玳安递到他手里,只掠了四五分一块与他,别的还塞在腰里,一直进去了。
玳安知道宋惠莲是西门庆的新宠,自己理当加以敬奉,但正如作者所言,宋惠莲本是“颠狂柳絮”“轻薄桃花”般的善于打牙犯嘴、对上对下全无忌惮的浅露轻浮之徒,如此颇具小家气派之人却自充主子,对其颐指气使,想玳安心中未必遂意。因此,即使在下人理当为之的凿银这类琐事之上,他同样要借机于讨好中刺痛惠莲,揭穿其老底。这种调笑戏耍的行为既以讥刺的形式排解了他的郁结之气,又因其谑而不虐的独到特质而不至于得罪惠莲及西门庆。当然,玳安这种对惠莲即看重又不齿的矛盾心理,恐怕和其主西门庆师出同门,不会有别。
其次,活跃于作品里的诸多伶牙俐齿的媒婆,其性格同样具有戏剧性的一面。《金瓶梅》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塑造了诸如王婆、文嫂、薛嫂等一批斡旋于男女之间的媒婆,她们擅长说媒拉纤,巧言令色,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形象。而在这批媒婆之中,又以王婆的形象最为精彩。
媒婆被列为“三姑六婆”的一种,历来为世人冷眼相待。由于她们说话往往天花乱坠、七虚三实,所以,一提到“媒婆”,往往总是会令久受世俗言论熏陶的读者心生憎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媒婆的这种职业特殊性要求她们能说会道善于说笑,客观上又增加了她们形象上的喜剧性。《秋水堂论金瓶梅》作者在分析王婆时,就曾指出,“我们一方面从道德层面厌恶王婆的狠毒奸诈贪婪,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从美学的层面赞叹这个人物的优美动人。”而“优美动人”的王婆形象,正是由人物本身的喜剧性所造就的。
第二回中,西门庆帘下巧遇金莲彼此有意,便至王婆处打探其虚实:
西门庆道:“干娘,你且来,我问你,间壁这个雌儿是谁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阎罗大王的妹子,五道将军的女儿。问他怎的?”西门庆说:“我和你说正话,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得不认得?他老公便是县前卖熟食的。”西门庆道:“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摇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对儿。大官人再猜。”西门庆道:“敢是卖馉饳的李三娘子儿?”王婆摇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双。”西门庆道:“莫不是花胳膊刘小二的婆儿?”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时,又是一对儿。大官人再猜!”西门庆道:“干娘,我其实猜不着了。”王婆冷冷笑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罢,笑一声。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西门庆听了,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么?”王婆道:“正是他。”
王婆明知西门庆之来意却先不动声色,故意先设下一个圈套,引西门庆这个她眼中为情而痴的“刷子”入彀。这种手法的喜剧性是极有韵味的:我们在设计了计策准备引人入彀之时,可能他的所作所为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此玩笑之行上获得愉悦。王婆的这种作法主观上固然是为了借机吊起西门庆对金莲的渴望与欲求,进而凸显自己作为牵线搭桥者的价值,以便从中牟利,客观上却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不期而然的喜剧化心理反应,尽管王婆言语所导致的结果早在读者意料之中。
这之后,在西门庆继续为达成己愿而不断试探之时,王婆依然巧妙地以言语逗引并操控着西门庆:
王婆做了个梅汤,双手递与西门庆。吃了,将盏子放下。西门庆道:“干娘,你这梅汤做得好,有多少在屋里?”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讨得一个在屋里!”西门庆笑:“我问你这梅汤,你却说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听得大官人问这媒做得好,老身道说做媒。”西门庆道:“干娘,你既是撮合山,也与我做头媒,说头好亲事,我自重重谢你。”王婆道:“看这大官人作戏。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这脸上怎乞得那等刮子!”西门庆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见今也有几个身边人在家,只是没一个中得我意的。你有这般好的,与我主张一个,便来说也不妨。若是回头人儿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个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门庆道:“若是好时,与我说成了,我自重谢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纪大些。”西门庆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两岁也不打紧。真个多少年纪?”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属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岁了。”西门庆笑道:“你看这风婆子,只是扯着风脸取笑!”
王婆先用“梅”与“媒”的谐音把话题转换到了西门庆所企盼又难以启齿的正题上,令其明白自己已了解他所求之事,却又不明确点破而是东拉西扯,故意用一些与西门庆期望南辕北辙的话语搪塞西门庆。这种不断落空西门庆期望的言谈自然仍是王婆谋财的一种手段,然而它同样亦是作者借对王婆性格的喜剧特点的表现来吸引读者的情节,这种期待与事态的不一致造成了整个语境的不和谐与悖谬,从而引发了喜剧效果。
浦安迪先生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将西门庆与潘金莲伤风败俗的偷情事件定义为为喜剧情节,他认为这一事件“使人读起来好像是一个古老而且妙趣横生的使人做‘乌龟’故事。……它却使读者只感到有趣。”浦氏的观点显然过于偏激,但我们应当注意其作出如是判断的原因是《金瓶梅》在此处描写上对嬉笑幽默及逗人欢乐的情调的确有自发的追求,其中,小说对王婆作为审美客体所具备的喜剧特点的强调便是这种独特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笔者拟以蒋竹山为例来分析《金瓶梅》中一类甚为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形象。
蒋竹山这一人物的名字谐音即“将逐散”,作者对这个形象的描写也印证了这个名字:蒋于小说第十七回在瓶儿请其为己诊治之时登场,至第十九回为瓶儿赶离,从此在小说中消失无踪,总共不过仅仅出现三回;然而这个一闪即逝的人物却能够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无疑再次印证了作者刻画人物手法的高妙。作者能够将蒋竹山这类龙套人物写的须眉飞动,离不开对其喜剧性的展示。我们不妨掇拾蒋竹山在小说中的言行并对其喜剧特点予以评述。
蒋竹山一出场,作者便以“人物飘逸,极是个轻浮狂诈的人”形容其品貌,自是一典型丑类。他在为瓶儿看病时便怀觊觎之心,先以言语相挑,见瓶儿言语松动竟不顾廉耻跪乞婚姻,全无医人之医德。其丑态如绘如见,令人可发一笑。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如此一个内存奸诈的无耻之徒居然还一本正经地攻讦本属一丘之貉的西门庆与胡医生的所作所为以自矜其德,这无疑是作者笔下最富于冷嘲热讽之处。正如崇祯本评语所言,“令人失笑,一味弄笔。”蒋入赘后陡然变富便开始招摇过市,买了一匹驴儿骑着,在街上往来摇摆,完全是一副得志小人的可笑嘴脸。然而瓶儿因蒋难满足自己欲望而对其情薄,加之西门庆略施手段,蒋竹山便倏忽间由空中跌落至谷底,显出其本来面目而黯然离场。作者下笔塑造这个极具特点的下层人物,实际上是借此对当时社会种种引发怪现状的丑类的自上而下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