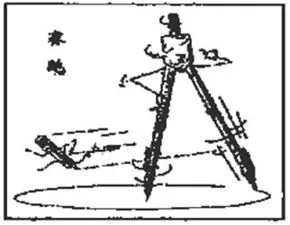阐释是什么意思,阐释学:“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对话还是误读?如何正确解读?
简介: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 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外国哲学专业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科学哲学。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思远道》、《泠风集》、《哲学科学常识》、《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等。
注:原标题为“谈谈阐释学的几个常用概念”,正文有所改动。
“一千个哈姆雷特”阐明以文本为起点,不以文本为终点。 所以,很多论者主张,阐明是完全开放的,一千个学生写哈姆雷特的感想,就会变成一千个样子。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想说:不是说明特有的现象,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 同样别人说的话很特别。 别人说的很特别,但只有一个扑克牌。 同样,看了一千人的样子后有一种感觉,但哈姆雷特只有一个。
哈姆雷特千部的感想中有千条花纹。 这是一个浅白的事实,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好事。 但是,这些感想既不是阐明也不是说明。 说明只是以文本为归宿,让其他读者能理解文本的说明。 这些感想,用张江的话来说,大部分不是“具有公共意义的有效说明”。 【张江,2019年】我看了庄子,每次都浮想联翩,我敢一字一句地解释庄子吗? 我们读书,大多数时候可能是自己乐意阅读,提高自己的知识,但从来没有想过能提高别人的知识。
读了之后,不是说明,通常不能说是说明。 每一种解构都侧重于生发、叙述,但每一种解构都与原文本有密切或松散的义理联系,受到文本的制约。 王弼对老子的解构可能比阐释更多,但他阐发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确实有很多联系。 由于存在这种联系,即使某种阐明已经脱离文本,也可能为文本的理解提供某种帮助。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写下了对他爱情的感想:既可以来自哈姆雷特和欧菲莉亚的爱,也可以来自奥赛罗和苔丝的莫娜,或者来自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哈姆雷特》会怎么处理这个感想呢不管它来自什么文本,它只是感想的触发。 其感想、奇怪和愚蠢对于理解《亨利四世》和其他文本没有任何帮助。
读书的爱好本来就多种多样。 随便看书,不太求解决,没什么不好。 陶渊明不是解经高手。 读了好几页书,引起了我的兴趣,高兴地下令动笔。 要是诗写得好就好了。 你不需要在意和旧书不相配。
莎士比亚读几部历史片段,写0103010,写0103010,都是传世之作。 请不要把它当成正史来读。 你做了你特有的哈姆雷特,真的做了,非常恭喜。 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区分解释、阐明和兴起。
“创造性误读”说明既然以理解原文本为归宿,说明就无法逃避是否正确的考虑。 说到阐明,对原文本的解读是否正确并不是主要的关注,如果新论有价值,误读原文本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后世的解释学倾向于称赞误读而不是允许误读,这种倾向集中在“创造性误读”之名上。
确实,如果优秀的新学说与原文误读有某种内在联系,这种误读可以称为“创造性误读”。 试着用哥伦布“发现”美国来摆脱阐释学,错误的认知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获。 但是,无论西方人发现美国的历史意义多么重大,哥伦布并不是有意犯下这个错误。 一个人故意犯错误,这件事相当奇怪; 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它属于另一个论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错过。 就文本解读而言,为了自我解释而故意误读,如果不欺骗社会上的盗名,那就会有意误导读者。
误读,无论是创造性,还是创造性,说的都是不小心误读。 进一步思考,只有无意中犯了错误才可能导致有效的创造,没有人会通过有意犯错误来创造。 所以,将错误的认知和有效的创造联系起来,一直以来都是外人的判断。 在“创造性误读”中支持故意误读,或者当事人实际用于为自己的误读辩护,都只是呵呵。
当然,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说明,包括不同的角度、不同级别的说明。 一个文本可以有宽、窄、深、浅的解释,但每个解释都必须误读才能成立。
我们不能把没有唯一的解释和没有正确的解释混为一谈。 存在独一无二的正确性的观念,最多只能有条件地用于物理学。 我不认为所有解读都是误读的主张值得认真对待。 其实,如果不正确解读这件事,就无法理解误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两类认知以上说明都是文本说明。 确实,无论是用中文说说明,还是用西班牙语说hermeneutics,本来都是面对文本的。 后来,解释概念传播开来,到海德格尔那里,解释不仅是人类的生存分析,在这里也被认为是解释学的核心。
这种扩张是随意的吗? 不。 海德格尔视域下,文本与这里有着重要的共同点。 要解释这一点,首先要区分两种认知。 两种认知是指其中的一种,被认知的东西是现成固定的,它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怎样认知它无关,如气温和气压、太阳产生光和热的机制等。 它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它,或者如何认识它。
另一种类型的认知是被认知的东西不是现成固定的,它跟我们怎么认知它有着内在联系比如,什么是幸福?
这个问题脱离不开我们对幸福的认知。幸福不是纯粹的客体,它随着怎样得到认知而改变。我们可以用同一个温度概念来讨论地球表面和火星表面上的温度,但我们用同一个幸福概念来讨论商朝人、宋朝人、希腊人或埃及人没啥意义。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一类认知,被认知的东西并非完全独立于对它们的认知;不仅如此,认知者自身也牵连在这种认知之中。一个人是否幸福,一个民族是否幸福,跟这个人、这个民族对幸福的认知有内在联系。这在自我认知或自我理解那里最为突出。
两个人有同样才能或同一种缺陷,一个人对之有所认知而另一个没有,这会使得他们是很不一样的人。对幸福、友谊、爱情、平等的不同认知牵连我们自己,牵连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牵连我们的存在、是、所是。简单说,这类认知是反身的认知。我们不可能考虑何为幸福而不同时也在考虑自己的生活,不可能考虑何为幸福的社会而不同时也在考虑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
我们都知道,在海德格尔那里,人,或者此在,不是现成固定的客体。对此在的认知包含上述双向牵连。然而,不仅人是此在,文本也是此在式的存在者。人们可能认为,文本阐释是这样一项工作:那儿放着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有一个真实的意思,阐释者努力去发现这个真实的意思,最后,成功的阐释就是符合这个意思,就像实证科学最后要符合它所研究的客体。
然而,上面已经反复说明,这正是近代阐释学努力摆脱的陈腐观念。狄尔泰一系旨在阐明,阐释学在根本上不同于实证科学认知。我们阐释一个文本,是要听到文本对我们说了什么,而文本说了什么,这不是一种现成固定的东西,在文本面前,阐释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参与到文本的言说之中;认知者和被认知者都牵连在同一阐释过程之中。
上述两种认知的区别,现在流行用Verstehen/Auslegung(理解/阐释)和Erklren(说明)来加以标识。近代阐释学思想的核心是理解。施莱尔马赫被奉为近代阐释学的创始人,主要在于他的阐释学首次聚焦于理解概念,从而使阐释学从技术指导手册转变为一门系统科学。
狄尔泰进一步把Verstehen/Auslegung(理解/阐释)视作“各门精神科学的通用方法”,视作系统精神科学的基础。(参见狄尔泰,2010年,第188、200页)狄尔泰的著作处处都表明,阐释学的这一发展跟那一时期自然科学长足发展的局面密切相关,可以视作精神科学在自然科学面前维护其自我认知:精神科学的认知“建立在生命表现与在生命表现中得到表达的内部状态之间的关系之上”,更进一步,这种认知还直接“建立在生命表现上”。
在狄尔泰那里,verstehen专指这种跟体验(Erlebnis)和“内在思想”紧密关联的认知,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与自然科学方法很少相似”。狄尔泰把理解或verstehen界定为“我们由外在感官所给予的符号去认识内在思想的过程”。(狄尔泰,2001年,第76页)显然,我们可以在体验的意义上理解他人、理解文本,但对太阳内部发生的核聚变过程的认知则谈不上这一意义上的理解——太阳发光发热不是符号,发光发热背后也没有什么“内在思想”。海德格尔对体验概念所含的心理主义因素有所警惕,但他说到理解,也始终不是活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那种认知,而是心领神会的认知。
在狄尔泰那里,作为“各门精神科学普遍使用的方法”,阐释概念的应用变得极为广泛。不过,狄尔泰仍然把语言阐释视作核心:
“我们将一定规则指导下的、对持久固定的生命展现所做的理解称为阐释。由于精神生活只是在语言中才获得一种全面、详尽,因为可以在客观上得到把握的表现,所以阐释的最高形态就是对于人类存在的文字记录所做的解释……关于这种艺术的科学就是解释学。”(同上,第198页)
在这个方面,海德格尔与狄尔泰稍有不同,在前者那里,基础的基础是生存论分析,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阐释学并不直接等同于生存论分析,而是依附于后者。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植根于在生存的生存论建构的分析工作这层意义上的阐释学,只可在派生方式上称作“阐释学”。(参见海德格尔,第48页)
无法否认精神科学认知和自然科学认知有系统的区别,不过,用Verstehen和Erklren,或用解释和说明来标识这一区别都不很自然。
Erkl?rung或explanation跟阐释的意思本来相近——hermeneuein的第一个意思是言说,第二个意思就是explanation。这两个语词的平常用法现在仍是这样——我们平常当然可以说“理解核聚变机制”之类,虽然核聚变并非包含着内在思想的符号。
但不管怎样,理解和说明所意指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看到阐释的对话性质。早在施莱尔马赫已经提出文本阐释具有对话性。后世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阐释不是阐释者单方面去理解作者,而是作者与阐释者之间的一场对话。
前面提到海德格尔在阐发赫拉克利特时曾申称“这残篇确在言此,虽未将此说出”,这也在于他把自己的阐释视作与赫拉克利特的对话,惟有这样一场“思想对话”才能把这一残篇未曾说出者“带入言说”。从追问与对话的维度来理解阐释,是阐释概念的进一步解放,为阐释活动敞开新的原野,使阐释活动变得更加自由。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自由同时也是责任。自由与其说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不如说变得更难。
在近世阐释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历史学家也常常从对话角度来反思历史研究,把历史学视作“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无休止的对话”。(卡尔,第115页)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话”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时髦语词。
由于时髦,把阐释称作对话颇为顺口,往往不再去审思其中的深意和疑点。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疑点:你批评一篇文章,作者做出回应,这是常规的对话;阐释通常涉及的则是古老的文本,作者已经不能出面来为自己解释、辩解——这也是柏拉图对书写这件事大有保留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说过之后就再不开口,只有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怎么能称作对话呢?
施莱尔马赫最早提出文本具有对话性的时候,并不是说作者会出面来回应阐释者,他说的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转变为讲者和听者,文本要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拥有的理解来解释。阐释学最早涉及的是圣经阐释或经典阐释。人众服从上帝的意旨,听从圣人的教导就好,没想到自己有什么资格跟上帝或圣人对话。
对话观念的兴起,依托于近代的平等诉求:阐释不再是普通人面对神谕时的任务,而是人面对人。把遥远的读者对古老文本的阐释还原到讲者和原始听众的说和听,拉近了阐释者和文本的距离。(参见何卫平,第188-191页,第199-200页)伽达默尔也是在这个方向上理解阐释学的对话性质的。针对西方哲学侧重于命题真理的传统,伽达默尔申言“语言最本己的存在不是在命题中,而是在对话中”。(格朗丹,第188页)
阐释的对话性质引导我们把阐释学真理更多地视为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而不是视为唯一的答案。在这个方向上理解阐释的对话性质自有启发,不过,这似乎仍然不是通常所说的对话:文本之后,接着说话的只有阐释者自己,最多,是阐释者之间在对话。
如果把文本视作现成事物,那么,文本一旦摆在那里,就不能再次开口说话。然而,如我们前面讨论两类认知时所尝试表明,有一类认知,在那里,被认知的东西并非完全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认知。文本阐释即属于这类认知。
文本不是物理对象,阐释不同于我们对物质客体的认知,文本阐释包含双向的牵连;文本和阐释者都牵连在阐释活动之中,互相发明——阐释既改变阐释者,也改变文本之所说。适当的阐释和阐发让文本翻出新意,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被阅读的文本也将经验到一种存在增长,正是这种存在增长才给予作品以完全的当代性。”(伽达默尔,第25页)作为精神客体,或竟作为此在式的存在者,文本随着阐释展露出新意义,这新意又呼唤进一步的阐释,阐释从而成为作者与阐释者之间的一场对话。
其实,我们常说的那句箴言,“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已经提示出这层意思。作品面世,是诞生而不是死亡;作品在与读者的交流中生存下去。通俗想来,我们今天对文本的解读,无论怎么高明,只能惠及今人和后人,无法惠及前人。但古人不得意,把自己的著述藏之名山付诸我们后人,我们若潜心理解了古人的真知灼见,也正可以说了却古人的心愿,让“过去和现在互惠地照亮对方。”(布罗代尔,第40页)
互相烛照并不要求看法一致。实际上,一方不断给另一方点赞,他们两个就不是在对话。看法不同才能形成对话,甚至看法相反也能形成有效的对话;质疑、反驳、生发新论,这些都属于对话。
对话不仅在开端处要求参与者有不同看法,而且,对话也不一定以获取共识为目标;鹅湖之辩并没有消除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根本分歧,但那仍然是一场有意义的对话。正因为对话并不要求始于相同的看法,也不要求终于共识,所以,真正的对话十分罕见,更常见的是披上对话外衣的各说各话。
让各个概念各归本己
日本学者久米博曾简明综述阐释学的近代发展:在施莱尔马赫那里,阐释学是一门阐释文本的学问;到狄尔泰那里,阐释学转变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到了海德格尔那里,阐释学从“理解的认识论”转变为“理解的存在论”。(久米博,第152页)至此,阐释学完全没入哲学,转变为哲学阐释学。哲学阐释学的兴发反映出人文探究的自觉意识,最终把所有精神事物的探究都囊括在阐释名下。
人的活动,人的产物,文本,这些都是精神存在,都含有历史维度,对所有这些的探究都以理解为核心。把它们收揽到同一个王国之内,有助于彰显经典阐释、文学艺术作品的阐释、历史学、社会科学诸种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更清楚地看到它们统统有别于自然科学。近世以来,科学主义盛行,科学研究方法广泛侵蚀人文探究,哲学阐释学所发展的一系列洞见有助于各门人类学科抵抗科学主义的侵蚀。
这一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前辈思想家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近世总体上不断加深反思的倾向。然而,我们今天回顾这个总体发展,难免也会发生一些疑问。
例如,久米博抱怨说,当阐释学转变成为“理解的存在论”,阐释学的原本问题,“解释文本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倒过来看,我们要问:Hermeneutik或阐释学是否适合于概括从文本阐释到此在分析这样广泛的探究活动?
这些精神存在之间有重要的区别。最突出的,是包括文本在内的言说和人事的区别。言说总是在吁请他人的理解。人的行为有时也是如此,例如建造纪念碑;另一些行为,由于牵涉到合作,惟当拥有适当的互相理解才能顺利进行。
尽管如此,人做事并不都旨在要人理解,用狄尔泰的话说,“行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行动者打算传达什么”。(狄尔泰,2010年,第189页)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大致体现出言说与行事的基本区别。从这一基本区别着眼,我认为不宜把历史探究乃至一般人类行为探究都揽到阐释学名下。文本阐释工作是一个边界大致清楚的领域,我会建议返回我们旧时的用语习惯,把阐释一词保留给这一领域,说到一般人事则使用解释这个词——实际上,直到今天,除了理论家,诠释、阐释这些词人们仍然只用于文本和话语,说到人的行为、动机、历史或“生存论结构”,人们仍然会用解释这个词。
在阐释范围内部,我的想法也相似。近代阐释学倾向于把概念从它们从前比较确定的用法那里松解开来。例如,揭示阐释的对话性质有助于我们看到,聆听文本之际,听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积极参与到文本的言说之中。这场对话把文本和阐释者双方都卷入其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活动场所。然而,有些论者听说了这些洞见,立刻把阐释等同于对话,把对话等同于读后感,沧海横流,反而掩盖了原始洞见。
然而,如前文所示,形形色色的参与并不都可以适当地称作阐释。阐释的目标是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本,质疑、反驳、生发新论,这些都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文本,然而,这不是它们的目标。阐释具有对话性质,但阐释不同于面对面的对谈。避免这种种混淆并不难,那就是把阐释叫阐释,把阐发叫阐发,把对话叫对话,让诠注、阐释、对话、误读这些概念各归本己。概念思考的一项任务是在一个概念之中揭示出它与其他概念的紧密的然而却隐秘的联系。这无疑让人兴奋。然而,只有当一个概念限制在它自身的意义之中得到使用,这些联系才会富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