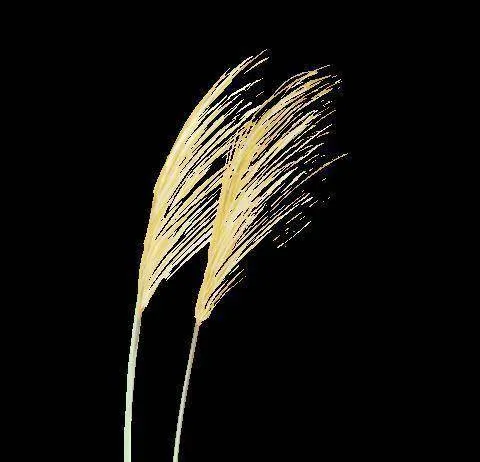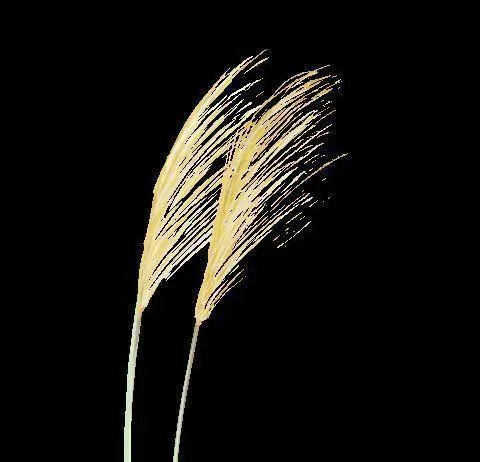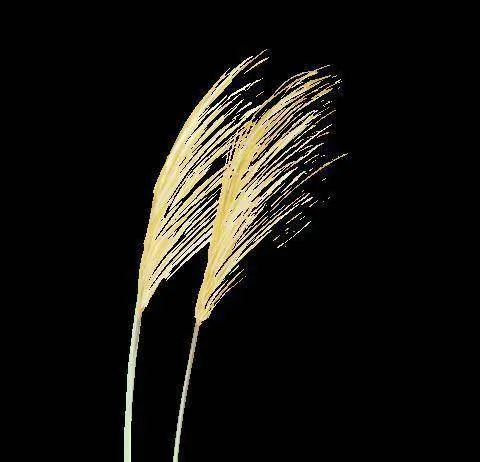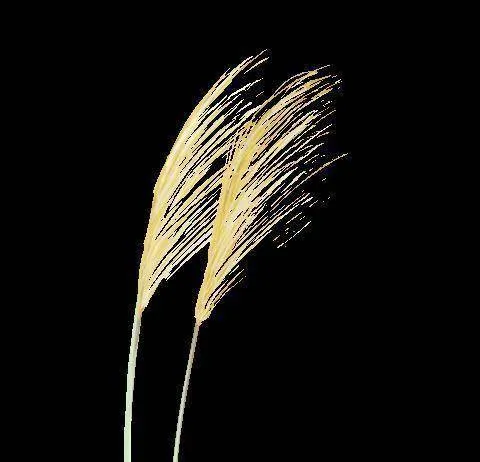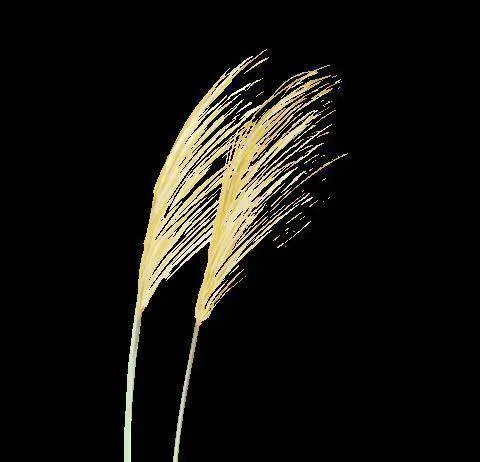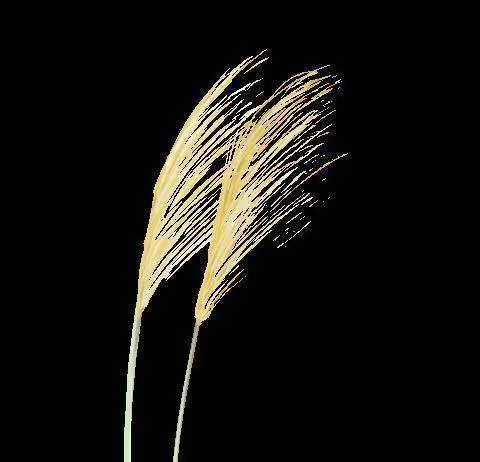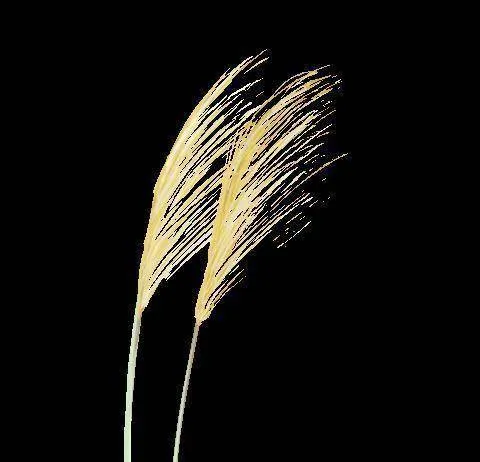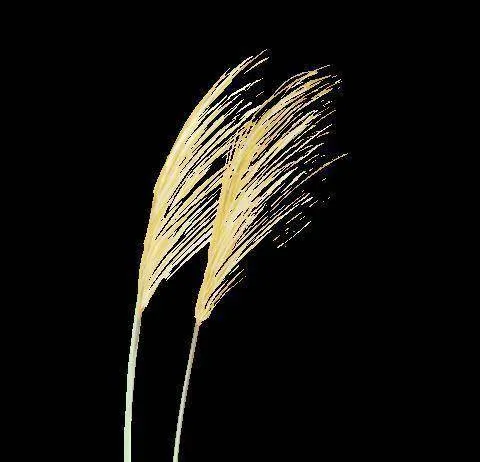《城南旧事》童年的离别之歌
本片以改编自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影片整体既没有连贯统一的中心贯穿情节,也没有明晰的时间线性故事和因果关系,而是采用了如同原著叙事结构的手法——散文式的缀合是团块结构,把三个故事情节时空打乱,再以第一人称的主角视角串联起来,形成独特的散文式结构,不以情节和冲突取胜,反而以“诗”的意境塑造出一首对童年的离别之歌。
1.叙事结构浅析
三个故事都以小英子作为第一视角展现,故事在完完全全的主观视角下展开和结束。意图在于不对客观世界加以任何评判,而以儿童的单纯视角去看世界,而世界的客观呈现,导演通过运用辅助型人物的方式加以解释说明,片中的秀珍房间外两个议论着她的女人中间的谈话,使我们知道了秀珍与爱人的过往;病房外传来的卖报声交代了母女两被火车轧死的结局。
这种结构的叙事方法能让观众清楚地看到事实真相,同时也和小英子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除了成人视角的复杂性后,单纯的去看待这三个悲惨的故事反而使人有更清晰的认知。影片一开头一段诗意的女声把观众迅速带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北京,“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随着画外音的落幕,影片正式开始。
2.电影中的“诗意”塑造
对于“乡愁”的表达,导演用一些回忆中的碎片式“意象”抒发出来: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剃头挑担声、用音响描绘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独特风貌,片头风声和乌鸦叫声,阵阵的驼铃声和水槽流水声,营造出岁月的流逝感,塑造着悲剧的氛围,秀珍她与妞儿在房里相认时,此时窗外传来火车的鸣笛声,使观众的心紧紧的揪着,去火车站路上的雨声、雷电声、马车驶过的声音、火车鸣笛声交织在一起,无不喻示着她们不会美好的结局。
李叔同的《骊歌》在本片中共出现四次,由第一次在片头的出现到最后一次片尾的再现,两次都以背景音的形式出现,达到了首尾呼应的效果,骊歌的四次出现,分别代表了主角不同的四次心境,怀念、愉悦、哀愁、悲伤,一次次将影片的情绪推向高潮,也表达出英子的人物成长。
3.视听语言分析
本片运用了大量长镜头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及氛围的营造,通过慢节奏长镜头的摇移,营造出一种哀愁的氛围,当秀珍回忆起往事,镜头慢慢的推至院子里破烂的窗户纸,停留一会之后,又慢慢的拉近秀珍爱人曾经站过的院子,然后又慢速推到窗户上,镜头第一次对准窗户,我们仿佛能看到秀珍眼里的爱意,曾经一起住过的房间是秀珍对爱人满满的怀念,而物是人非,第二次的对准,我们又能看到这个女人的痴情,能看到她的等待。英子出院后,和父母一起坐着马车去往新家的路上,一个长长的跟镜头跟着这辆马车,英子问父母,“那过去的事呢?”父亲说:“过去的事啊,慢慢就忘啦。。”此处的长镜头设计让我们好像也进到英子的视角中。在片尾,长工坐着马,渐渐的远去,小英子也坐着马车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我们视野,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枫,这两个呼应的固定长镜头配上抒情的《骊歌》,也让我们感到离别的凄凉。
影片的基调是怀旧的暖黄色,老老旧旧的黄色迅速把人拉回那个年代,服装是素淡的,景物也是暗淡的,但红色作为一种符号式的颜色几次出现在片中不同角色的身上,如第一个故事中,英子首次出现时穿着一身红袍,嘴里学着骆驼嚼草的样子,甚显可爱灵动,而当红色出现在妞儿身上时,是她的养父跟在后面推搡她的情节,红色长袍对于妞儿来说寓意并不像英子一样是鲜亮、活泼的,而是悲惨的,更加凸显出在时代背景下的两个同龄女孩之间的不同地位;秀珍在屋里怀念起爱人,翻出自己给孩子做的红色的玩具和衣物,可见红色在秀珍身上的体现与妞儿一样,都是悲惨命运的体现。通过这种同一颜色下不同含义的对比方式,让英子和妞儿的命运在冥冥中画上了一条浅浅的分界线,让大家看到了现实对下层社会的压迫。
景台打水、乌鸦啼叫等画面和声音在片中数次出现,这种重复蒙太奇的运用象征着小英子的生活一天一天过去,她也一天天的长大。象征和妞儿友谊的小鸡、秋千,每次出现都体现着英子不同的心境,或童贞,或想念,最后一次出现在英子告诉妞儿她的身世之谜上,当妞儿转身离去,画面呈现出空荡荡的秋千上,和着窗外的雨声,一切不言而喻——将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临。小英子一次次跑去废弃的草地,和盗贼的感情在一次次的重复中起了微妙的变化,一直升华着主题。
结语
一影一话谱人生虚实
俱是覆舟风雨书字可抵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
终南影话电影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