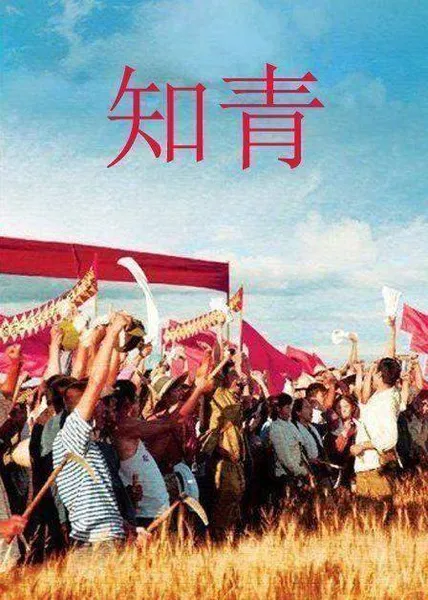为什么梁晓声对《人世间》的改编不闻不问?他早就有一个预料
非也。
梁晓声有着非常明确的剧本创作意识,这在作家队伍中,并不多见。
《年轮》中的小姨情节雷同于《黑纽扣》
后来,梁晓声写的《知青》、《返城年代》都是按剧本来创作的,里面的心理刻画都相对薄弱,整个文本中,充溢着对话体的语言形式以及频繁的适应电视剧的转场跳跃。
《知青》在2012年被拍成电视剧,这部剧中采用的素材,像《年轮》一样,都是之前梁晓声写过的内容的拼盘,新鲜度严重不足,他用八十年代的素材改写成电视剧剧本,在内容上已经不具备新意,所以这部电视剧反响平平,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
梁晓声对《知青》受到的冷遇,很是愤愤不平,当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连问了几个问号,很有一点不受待见、非要讨一个公道的意思在内。他反问道:“难道我拍之前还得问问他们是不是感兴趣?现在那种戏说的、穿越的电视剧还少吗?难道我非得满足这些观众的口味吗?难道他们的口味很重要吗?”
在反问的同时,梁晓声也意识到他的写作太过于急功近利化到已经偏失了他的写作宗旨,那种剧本体的写作,已经淘空了他的创作深度。
于是,他发愤在《人世间》里重归文学本体,注重社会风貌与人物心灵的揭示,这些内容,在剧本体文本里是一笔带过的。
你要改编,就必须把“回形针”拉直,满足影视改编的线性故事发展要求。
在《人世间》原著里,最完整的情节线索就是郑娟身上缠绕着的汇合了多个男人的纠结纠葛,这个情节主线,一直牵连到周楠的结局问题。
电视剧达到了情节线尽量延伸的目的,但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秉昆与骆士宾的冲突动机给改得面目全非了,原著里,秉昆与骆士宾拳脚相加,是因为想夺回周楠,此时的秉昆是没有退路,只能放手一搏,他的动机包含着爱的攫取与保护这一个心理动因在内。现在电视剧改成了周楠此时已经逝去,秉昆与骆士宾之间已经没有了争夺儿子的强烈动机,只是两个人在机场上见面之后一语不合而动手互搏,失手导致了骆士宾意外受伤直到去世。
之后,电视剧又设置了一个秉昆与父亲的冲突点,这就是周父带领全家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地拜年,秉昆跟在后边,倍感周父招摇过市、显摆得瑟背后自己的身为老疙瘩的失落,为此,他与周父产生了语言冲撞,认为父亲拜年是一种显摆,反向地是突出了自己的地位卑微。此种矛盾线一直延续到秉昆送周父到火车站上,父子俩矛盾加剧,不欢而散,各奔东西。
至少,王海鸰把梁晓声不抱希望的影视改编,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一件叹为观止的大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