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完美也可以,甚至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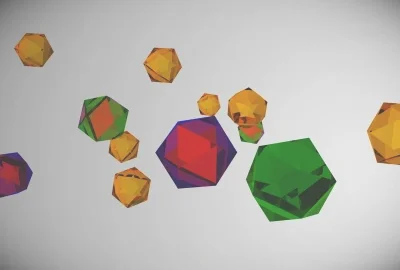
◎戴晨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书写女性寻求独立、彰显个性、实现价值的大女主,在影视界已经不是新概念。近些年热播的人物传记剧、古装仙侠剧、都市情感剧、职场剧中,事业有成、人格独立、励志图强的女性,已经成为影视剧的主流形象之一。
在同样的社会思潮下,大女主形象也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着龙袍的霸气女皇,身披铠甲的女中豪杰,穿旗袍的民国绝世才女……话剧《德龄与慈禧》、京剧《大唐贵妃》、舞剧《昭君》《花木兰》、昆曲《林徽因》等,从历史中汲取素材,演绎传奇女性。而话剧《桂梅老师》、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等,则选取了当代生活中的女性英模人物。
这些女性角色有的集美好于一身,甚至“完美无缺”;有的身上闪烁着崇高的光芒,独立自强。但是,观众看多了光鲜亮丽和伟大传奇,终归要由远及近落脚于对眼前的追问和审视。
顾雷编剧、导演的话剧《长翅膀的杜若》,塑造了一个反常的母亲形象——杜若常年生活在阁楼中,不施粉黛,佝偻着背,邋邋遢遢,刻薄计较。丈夫刚去世,她竟畅想起未来的新生活——烫头、镶牙、跳舞。儿子无法接受母亲瞬间放飞自我的态度,矛盾不断激化,随即牵扯出深藏于这个家庭的伤痕:母亲年轻时热爱舞蹈,光彩照人,但因为女儿的意外去世备受打击,跳舞也因此被视为一种“诅咒”。往后余生,母亲放弃了跳舞,如折翼天使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两代人之间的牵绊向观众抛出一个问题:一个女性成为母亲后,是否有资格为自己而活?
人老了就得放弃追求梦想?当了母亲,当了外婆,就应该停止探索自我、探索世界的脚步?中国的老年女性一直被忽视、被符号化,而杜若身上那对“隐形的翅膀”,成为重塑自我、重新生活的象征。有些遗憾的是,结尾虽然母子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杜若并没有真正拾起高光时刻,而只能在另一个自由之境遇见年轻的自己。
杜若不同于舞台上大部分的女性形象:她既不光鲜亮丽,也没有传奇一生,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她足够真实,足够令人心疼。
近日,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了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晚安,妈妈》,营造了一个看似温馨的生活场景。观众刚刚坐定,女儿就率先发出了预告:“妈妈,我要自杀。” 是的,不要怀疑你走错了剧场,这里并没有“母慈女孝”的戏码。剧中这对母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撕破了传统意义上母亲与女儿的亲密关系。
她们代表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的种种错位。多病离异、事业无成、生活一潭死水的女儿,在自杀之前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最后的梳理,与妈妈展开了一番关于人生的长谈。二人的极限拉扯夹杂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也有短暂的温馨回忆,但依然无法避免歇斯底里的争吵。而妈妈对女儿从觉得不可理喻到奋力挽留,也最终化为无力的妥协。随着一声坚定决绝的“晚安”和一声枪响,女儿选择与世界告别,妈妈选择了继续活着。她们此时此刻不再是谁的母亲、谁的女儿,而是回归于生命个体本身。
《晚安,妈妈》没有给剧中人戴上道德的枷锁,没有对谁的行为进行歌颂或批判,而是在哲学层面讨论女性对于生命的选择权。该剧联合导演唐烨说:“在同一屋檐下看似最亲的母女两个人,怎么就过成了陌生人?原来我们总是呼吁要尊重生命,现在我们开始关注活着的尊严、价值,甚至去主动选择的权利。”
此版《晚安,妈妈》场景极尽还原真实生活,水龙头能拧出水、冰箱里塞满食物、杯子盛着冒热气的巧克力饮料——这些细节扰动、感染着观众的情绪。创作者并没有追求表面化的女性主义,也没有刻意本土化,而是通过剧作扎实的结构和台词,为作品赋予了理性又感性、克制又具有张力的气质,塑造了两个复杂多义的女性——两个不完美的女性,甚至带着残酷的色彩——在她们身上投射关于个体、家庭、生命、尊严这些永恒的命题。
当今女性的性格心理、人际关系、痛点都比以往更加多元,她们的精神世界显然需要更深切的关注和展现。《长翅膀的杜若》《晚安,妈妈》的上演,让女性褪去“完美”滤镜,构建自我认同,为女性戏剧注入更多内涵。《晚安,妈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作,距今已经40多年了,希望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女性形象还能有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