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快讯】王世襄与一份“无奈的合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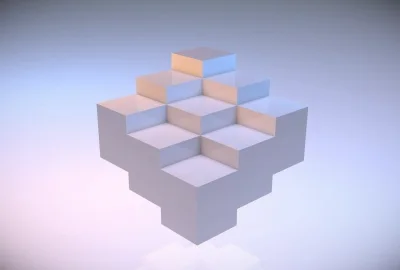
我是到香港以后才认识王世襄先生的。当然早闻他的大名,一直无缘相识。而真正有机会见到他,却是在他与香港三联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很有几分尴尬。
这显然是对知识产权的误解,为此王老觉得十分委屈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1996年底,我刚到香港三联任职,出版经理关本农就告诉我,王世襄先生因为对香港三联不满,要解除《明式家具研究》一书的出版合同。
深入了解问题的缘由,我知道王老对三联的意见,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一本书,而是因为此前他在香港三联出版的图册《明式家具珍赏》,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问清原委后,我明白事情不怪香港三联。根源在1985年香港三联和北京的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无奈的合约”(王世襄弟子田家青语)。因为那时没有《著作权法》,合约签得很不规范,虽然署名王世襄主编,却是由文物出版社代行签字(甲方),将这本书的版权(包括中文和各种外文版权)永远转让给了香港三联(乙方),合作条件是:甲方提供画册全部照片和文字,由乙方设计和印制。乙方须以实物向甲方(文物出版社及王世襄)支付报酬,这就是赠送甲方半成品(全部印刷完毕的图书正文内页)1400套。这一条,香港三联是如约履行了的。也就是说,香港三联付过稿酬。
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
其一,这样付酬合理吗?以我的了解,合作出版,以实物(成品或半成品图书)付酬,作为香港和内地出版社之间合作的模式,是符合惯例的,至少在当时。
其二,这样合作是不是甲方(包括王世襄和文物出版社双方)吃了大亏?我测算了一下,1400套半成品,大约折合14万元港币,这在80年代中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作为稿酬,数倍于当时一般图书稿酬的标准。这笔钱可以说,无论对文物出版社还是王老本人,都是可观的收益。那时王老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200多元呢。只不过,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将这些半成品的正文内页装订成书到市场上销售后,并未向王老支付稿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书中全部照片的拍摄者和版权所有者,拥有画册的版权,王老只是他们请来的主编,于是仅用赠送100册样书向王老付酬。
这显然是对知识产权的误解,为此王老觉得十分委屈,认为自己被两家出版社特别是香港三联坑了。他不知道他的稿费应向文物出版社索取,也不知道香港三联为出版此书曾经承担很大的经济风险,前期的制版费用已十分昂贵,后期的印制费用更是惊人,这曾经引起出版社一度亏损。他只是了解到此书经过大力推广后接连重印并向台湾地区和多个国家售出版权,香港三联收入颇丰,觉得自己的利益被侵害,愤愤不平。本来,这份合约规定他的学术著作《明式家具研究》也按这种模式和香港三联合作,但王老为了保护自己权益,立即要求终止合作,在补偿了文物出版社一笔拍照费用之后,成功将《明式家具研究》的版权收回,于1989年2月和香港三联单独另行签订出版协议。
这样,关于另一本书《明式家具研究》,王老和香港三联的合约,就是完全符合国际出版规范的。出版前,由香港三联一次性向作者支付文字稿费和照片使用费共计港币6万元,另附英文版稿费5000美元,两项合计达10万港币,合同期限8年。但是,就在我到香港工作的第一个月,因为这份合约即将到期,王老来信通知香港三联,准备结束合作。
当年那份“无奈的合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我第一次见到王世襄先生,算是巧遇。1997年春节过后,我赴港后第一次回北京出差,抽空到北京三联拜访董总,谈话中推门进来一位老者,身穿灰色棉衣,围着黑色的长围脖,头戴皮帽子,他就是王世襄先生。
董总介绍后,我递了一张名片给王老。告诉他《明式家具研究》这本书,我们还希望和他续约。他听了似乎很高兴,并没有坚持说要收回版权。他说话非常客气,告诉我,他会给我写信,有事在信里商量。
我回港后不久就接到了王老的信。他写信用圆珠笔,字迹非常工整,而且用复写纸拓写。为了这本书续约,他大约给我写过五六封信,每一封都如此。我猜他自留底稿,是要留下证据,以备发生版权纠纷。他那时对香港三联的戒备之心非常重,当然这和我个人关系不大,他主要是对三联的老一代领导人、前总经理萧滋先生误解颇深。但这样一来,我们洽谈续约就不顺利了。
在这种情况下商谈继续合作,我们当然需要格外善待作者。和赵斌总经理商量以后,我们主动提出把原先的稿费制改为版税制,重印时按10%的版税付酬,这样老先生可以比第一版出版时多得几倍的报酬。王老欣然接受这一条件,但是,对于我们提出因为香港市场太小,图书销售很慢,准备重印3000册,并考虑将其中一部分销售到中国内地,老先生却不同意,他表示,如果有一部分卖到内地,就一定要印5000册。我几番去信解释,他都不肯让步,一时双方僵持。最后老先生来信,说双方各退一步,按4000册印,一言为定。于是我们寄上合同,王老签了字。
续约条件谈好了,但香港三联发行人员听说此事,意见颇大。他们说过去8年总共都没有售完3000册,未来5年怎么可能销售4000册?新书变成旧书,销售只会一年比一年少。于是我们只得重新研究,压下合同暂未签字。谁知过了两个月,王老没有收到寄回的合同,又急了。他对我们的诚信提出质疑,怀疑我们利用他先签字搞什么鬼,来信中把话说得极其难听,有点老账新账一起算的味道。于是我对总经理赵斌说,此事恐怕不能再耽误下去。赵斌觉得,事到如今,哪怕是苦果也要吞掉,所以同意就按4000册签约。我算了算,这笔版税总共约32万港元,若是书压在库里,是难免造成亏损的,但是想到王老对香港三联的一腔怨气,我们以为需要安抚老先生的情绪。赵斌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王世襄没有从文物出版社拿到报酬,我们在《明式家具研究》上多给他一点,算是我们的心意。”
不过,王老大概不会领我们的情,这是在商言商的谈判,何况,两本书的报酬原本就各不相干。但是,香港三联以这样的条件签下《明式家具研究》的续约协议,真的是在作亏损预算,当时就可以预见,这盘棋没有胜算。这样做的结果,是到了2002年合约再次期满又要续约时,由于库存尚多,我们已经无法承诺再次重印此书。于是香港三联关于《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与王世襄的版权合作只能到此结束。
然而到了这时,王世襄先生也感觉到需要解决《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版权问题了。当年那份“无奈的合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中国的《著作权法》还没有实施,如此的版权合作无法可依。但是现在,一切都可以在法律框架下重新研究解决。所以在2002年底,王老委托了律师,分别与文物社和香港三联交涉,整个过程,我是直接参与者和当事人。
我和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通了电话,都觉得这件事用不着诉诸法庭。尽管那份“无奈的合约”是无期限的授权,原本没有“结束”一说,尽管文物出版社作为图册中全部照片所有者确实也应享有一部分的作者权益,尽管香港三联当初花费数倍于基本稿酬的巨资签下如此协议是为了买断这本图册的全部版权,但到此时,我们都不愿意再斤斤计较了。于是我们两社和王老共同起草了一份协议,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两社都声明确认,王世襄本人是《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唯一合法的著作权人,应依法享有著作权人的全部权益。王老则主动表示放弃对香港三联和文物出版社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出版“珍赏”或授权他人出版“珍赏”行为的“任何版权诉讼请求权”,同时放弃对两社此前出版“珍赏”所获得利益的追索权。于是围绕《明式家具珍赏》的版权纠纷至此了结。此书后来由王老另行授权文物出版社制作出版。
版权问题是顺利解决了,但是不能不说,在这场纠纷中,有一个人却承受了难言的委屈,他就是香港三联的前总经理萧滋先生。
明式家具热潮,从香港掀起;明式家具走向世界,从香港出发
不少出版界同行都知道,萧滋先生对于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是独具慧眼的。隆重介绍王世襄先生,萧先生可谓有胆有识。
1982年,萧滋和香港几位出版界同仁一同到北京组稿,在文物社提供的选题目录中,他一眼看中的就是王老的著作。据他自己解释,他是因为早年做外文图书进出口工作时,曾经注意到德国学者艾克用英文写的《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在香港和欧美市场上都受到关注,表明中国家具已经开始进入收藏家的视野。他由此相信这种题材的书,在香港这个狭小市场上应该是有条件出版的。
但是,王老当时交给文物社的著作,与艾克那一本不同,它不是关于明式家具的图册,而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大部头学术著作。萧滋担心此书以如此面貌出版会造成经济上的较大亏损,所以大胆建议,把这部著作一分为二,首先沿用艾克那本图册的思路,将著作中的图片抽出来编成一部以图为主的大型图册,待图册产生影响后,再集中力量打造一本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这样前一本图册如有盈利还可以补贴后一本学术著作的亏损。萧滋的建议得到文物社和王老本人的认可,于是王老的著作便被拆分成《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批出版。
从经营策略上讲,萧滋的策划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当时并不能确保明式家具的图册可以盈利。他的测算,是即使盈利,大概也要在重印并售出海外版权之后,而并不是立即可以见到。但这些话,他并没有告诉王老,更没有说香港三联即使是先做这本图册,按照与文物出版社合约规定的合作模式,也仍然承担不小的经济风险。以至于王老从来没有意识到萧滋选择出版《明式家具珍赏》,只是因为看重了这部书的艺术和文化价值,而并不是为了赚钱。王老不了解,作为一个在香港备受敬重的文化人,一个著名的出版家,萧滋一生都从没有把赚钱看得特别重要。
无论如何,大型图册《明式家具珍赏》的出版成功了。1985年8月,王世襄先生亲赴香港参加《明式家具珍赏》新书首发式,一时引起轰动。这是中国人有关明式家具的著作第一次呈现在世界面前,王老为此非常振奋和激动,他为萧滋先生题词:“从此言明式,不数碧眼胡”,意思是说今后研究中国的明式家具,要看中国人自己写的著作了,显示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愉悦,而他给责任编辑黄天的题词“先后奋战,共庆成功”,表明他对香港三联的编辑出版工作十分满意。
但是,因为出版后没有拿到稿费,王老对香港三联的态度顿时有了很大转变。由于不能了解香港三联的经营情况,所以他内心中的猜疑转变为对萧滋的误解和怨恨。不久萧滋退休,王老致香港三联新任总经理的信这样说:
“大家都清楚:当时了解《明代家具珍赏》一书的国际行情,可以出多种文本及一文多本(如英文本就有五个)畅销全世界的是萧滋先生。瞒着作者,将他蒙在鼓里,和文物社搞非法交易,用1400本画册内文页换取作者所有的世界各种文版的版权,也是萧滋先生。大陆作者多年出不了书,对《版权法》又一无所知,因此有机可乘,只须略施小技,给点小恩小惠,便可使他俯首帖耳,感恩不尽,捞到大便宜;了解以上情况的也是萧滋先生。总之,萧先生的精心策划,掘了陷阱让人跳,实在不够朋友。尽管他为贵店捞到了便宜,但实在不光彩!他本人和贵店必将为此付出代价,至少是声誉上的代价!”
这分明是说,萧滋为王世襄出书根本是一个阴谋,而香港三联也参与了坑蒙拐骗。
这些话对萧滋先生的不公平显而易见。但萧滋本人当时对王世襄的态度只是风闻,不得其详。直到大约15年后,就是在王老和我们解除《明式家具珍赏》合约的前后,王老为了了却这桩心事,做了两件事:一是将那份“无奈的合约”交给他的入室弟子田家青保存,嘱田在将来适当的时机发表出来,立此存照,以鉴后人;二是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把他心中关于《明式家具珍赏》的苦水尽数倒出。这篇文章引用了他上面这封信,被萧滋看到了。
萧滋先生的心显然是被狠狠地刺伤了。当时我正在香港三联主持出版工作。听到三联很多同事议论,大家都对萧滋抱以同情,给他以安慰。
平心而论,王世襄著书立说,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没有得到应有回报,他的不满和愤怒,我们都能体谅,他有火气要撒,我们也能理解。但这既不是萧滋的过错,也不是香港三联的责任。相反,应该承认王世襄是从香港三联走向海内外,走向全世界的。香港三联以达到国际水准的图书制作形式,将这两本著作推向国际市场,奠定了王世襄作为“明式家具学”创始学者的尊崇地位,使其赢得了全球文博界的高度赞誉,萧滋作为出版策划人和主持者,功不可没。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黄天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这两本书在香港出版,使香港获得先机,很快便成为明式家具的集散地:多少家具珍品由此出口海外;但若干年后,又回流香港,甚至重返内地。明式家具热潮,从香港掀起;明式家具走向世界,从香港出发。他所讲的情况,大抵符合事实。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推手,正是萧滋先生。
《中华读书报》那篇长文发表以后,我和萧滋先生几次提起此事,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心结。劝慰的同时,我想请他撰文澄清事实。但没想到这位儒雅的老人只是付之一笑,说:“是非功过,由后人评说吧。”
“萧滋也有委屈,为什么我不能替他说呢”
此后又是十几年过去,这件事差不多被人淡忘。谁想因为王世襄弟子田家青出版《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按照王老的遗愿公开了那份“无奈的合约”,使得《明式家具珍赏》的版权纠纷再次成为媒体话题。
一直缄口不言的萧滋先生已经年过90,但这次他有点忍不住了。此时我已经返回北京多年,萧滋先生给我来电话,讲了自己内心的感受,说:“在《明式家具珍赏》这本书上,王世襄的确吃了亏,我觉得不好意思,所以30年中他讲了那么多骂我的话,我都没有回应,我觉得这是历史造成的,就让它过去吧。可是田家青又把它翻出来,我不能不说清楚了。”
于是萧滋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回忆性的长文,说明当年香港三联是怎样费尽心力把《明式家具珍赏》做成传世经典的。老先生依旧保持儒雅风范,他没有去争辩什么,只是讲自己做了什么。文中虽然提到香港三联为了制版花了14万港元,相当于香港普通人家半套单元楼房的价钱,但是既没有公开当年的成本和效益账目,也没有讲述发行此书先亏后盈的过程,甚至没有提到当时香港三联承担的经济风险,更没有说明三联曾经向甲方(文物出版社及王世襄)以实物形式支付过巨额稿费。我读了文章以后,打电话对萧滋先生说,有些话也许他不方便说,我来写文章帮他说吧,他未置可否。
我联系了田家青,责怪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书中刊出这篇“无奈的合约”,他说,这是王世襄先生正式托付给他的事情,他怎么能不履行责任?田家青也是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的骨干作者,与我关系甚好,联系也相当密切。他对我很信任,写了文章常常会提前发给我,听取我意见和建议。他这本《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我在北京三联工作时出版的,稿子我曾经看过,但看的只是文字稿,而“无奈的合约”是一个加了说明的照片插图,我在发稿前未曾见到。现在印在书上,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萧滋先生。便对田家青说,关于王世襄与萧滋之间的恩怨,我恐怕要写一篇文章。田家青回说:“你可别写,你如果写了,我还得回应,那么咱们两人不是打起来了吗?”我说:“我只讲客观事实。王世襄有委屈你要替他说,萧滋也有委屈,为什么我不能替他说呢?文章写好了我先给你看。”
后来,我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王世襄的版权公案》,全面回顾了这本图册出版的前前后后,分析和评论了“无奈的合约”产生的缘由,对王世襄先生的维权行为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时强调作者被侵权的责任并不在香港三联一方,萧滋先生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我把文章寄给田家青过目,他没有表示异议。
于是我在《南方周末》发表此文,引起一定反响。萧滋先生看了,电话里连说谢谢,谢谢。我想,这篇文章大概将他的心结解开了。
几个月后,我到香港看望萧滋先生。他握着我的手,很用力,两眼深情地望着我。聊天聊到一半,他忽然进入内室翻箱倒柜。起初我不知他要找什么,等他拿出一只卷轴,才明白他又要赠我墨宝。他是知名书法家,作品在香港大会堂展览时曾经获得大奖。这次他拿出来的是一幅以一丝不苟的工整的小楷临写王献之的长卷作品《洛神赋》,文末有跋曰:
“晋王献之小楷洛神赋传至唐代只存十三行,余已临习多遍,兹试以大令笔意书写全文,如能得其十一于愿足矣。”落款为“戊子初春萧滋书于香江”。
他展示后很郑重地赠我,嘱我收藏,说是留个纪念。他强调这是他十年前的作品,是自己最满意的一幅,同样的水平,现在已写不出。我被此情此景深深感动,受宠若惊,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