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扎的世界,每一个“我”皆不可逃-全球观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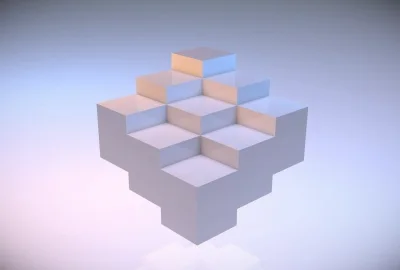
◎张之薇
【资料图】一部戏曲作品的成功永远离不开与剧种相贴合的地域文化的滋养,更离不开可以点燃它地域风格魅力的那个创作者,老舍之于曲剧,就是这样的存在。继过往将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龙须沟》《茶馆》等作品改编成大戏之后,北京市曲剧团这次再从他的作品中寻找灵感:编剧胡铭帅、导演白爱莲,以及北京市曲剧团一群年轻的新生代演员将其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搬上了曲剧的舞台,重新为老舍笔下的“我”塑形铸魂。所不同的是,这次选取了“小剧场”这一更加自由、更具探索性的打开方式,创作者借助经典文学的力量让曲剧的魅力在舞台上充分展现,令人沉醉。
纸人:从原著中升华出的全新形象
从戏剧的视角来看,小说《我这一辈子》是极其平淡的。老舍以“我”的第一人称形式娓娓讲述裱糊匠这一辈子的遭际,讲一个少年学手艺,青年靠着手艺过上体面日子,壮年却遭遇妻子与师兄的背叛、改行干巡警的营生,中年之后却仿佛掉进了窟窿里一路下滑的故事。令人琢磨的是,老舍文字本身的平淡,并没有抵消在大时代浮沉中的“我”的巨大辛酸,反而为读者树立起一个不具姓名、平凡而又卑微的个体。当代文学家夏志清曾言,老舍是一个“对个人命运比社会力量更要关心”的作家。虽然,这是对老舍1937年之前作品的总体评价,但是,写于1937年的《我这一辈子》,以时代之小我为切口,还是揭示了人生存的普遍困境,那就是人在命运漩涡之中挣扎的徒劳。
曲剧《我这一辈子》的创作者不仅准确地抓住这一主旨,更令人赞赏的是,他们还从老舍先生平淡的文字中升华出一个全新的舞台形象——纸人,实现了文学向舞台的转换。全剧在“我”与纸人的博弈之间展开,初登场的“我”在纸人面前的优越感溢于言表,自视有血有肉,懂得场面,手艺傍身,娶妻生子,享受着做人的幸福,好不得意,此时的纸人在“我”的面前不过是手中把玩的活计。随着大清国的崩塌,西风东渐,裱糊匠的手艺渐渐派不上用场,连自己头上的辫子都难以保住,又突遭妻抛子私奔,想做一个人的“我”开始不知所措。曾经在自己手中打造出来的光鲜世界,就如他手中的裱糊活计,不过是一个可能瞬间倒塌的世界。纸人与“我”的力量开始逆转,人世间原本就是一个纸扎的世界,每一个想与命运抗争的“我”,都无法摆脱时代与社会的裹挟,无情的社会只能让人不可控地深深坠落。那个在老舍笔下没有姓名、不信命的个体,在曲剧《我这一辈子》的主创笔下,在与纸人们的周旋之下,最终也难逃沉沦、幻灭、成为灰烬的结局。
“我”与纸人的对抗,生出莫名的悲凉
近年来,歌队的使用在戏曲作品中并不少见。该剧中,导演以纸人为歌队,让扮演和叙事自由切换。但创作者更深层次的用意是,以纸人为对立面,用舞台表现手段创造出“我”与“我”所处的外部社会的冲突。纸人的世界,就是一切外在于“我”的世界,是一切与“我”形成对抗的虚无、无形的力量。当这种不可名状的无形将“我”彻底打败的时候,自然升腾出一种莫名的悲凉感。这种悲凉感是与老舍先生的原著相通的。
导演形象化地将外部社会的魍魉魑魅幻化为舞台上的纸人,纸人的世界是机械顿挫的、歪歪斜斜的、没有表情的、身着面具的,他们与表象光鲜亮丽、有血有肉的“我”形成巨大反差。但是每一次“我”的失意和沉沦都离不开一群纸人的嘲笑和喧嚣。当舞台上的“我”的身上也仿佛长出了提线,在纸人们的控制下无法站立、东倒西歪的时候,实际上是导演用演员的肢体表现完成“我”与纸人的冲突。所以,《我这一辈子》中的纸人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夸张变形的纸人舞蹈起到了点明主题的作用;纸人世界的交流充满荒诞性,却又极具哲理;而纸人和“我”的对话,则昭示出现实本质和生活表象分裂的残酷性。
值得提及的是,与怪诞荒谬的纸人世界并存的是小锁这一人物,以及开场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那只娴静的小猫。导演让饰演小锁的演员与仿佛置身世外的小猫合体,显然是有隐喻性的。剧中的小锁,是“我”之外部世界里最无邪的存在,却瞬间惨死;而那只小猫所呈现出的一份安静温柔,更反衬出了人世间的惨烈。
曲剧进入小剧场的新鲜色彩
文学性的再创造,是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成功的第一步。而更不可忽视的,是小剧场的观念赋予了这部戏曲作品更大的探索性和实验性。这不仅让戏剧的魅力在戏剧场的空间之下发酵放大,也为曲剧插上了翅膀。
以单弦牌子曲为唱腔母体、以北京方言为念白发展起来的北京曲剧,以长于叙事的说唱表演为特征,并且没有太严密的戏曲程式负累,加之曲艺的腔调、京腔京韵的地域风格,都注定它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戏曲形态。然而,北京曲剧在北京观众心中的边缘位置却不可回避。《我这一辈子》在2022年艺术创作萎靡之际给人以一抹亮色。它以小剧场的形态进入,赋予了年轻的主创和演员更自由的精神,他们的创造力、对艺术的赤诚,是与年轻的戏曲观众相通的。
剧中,对纸人歌舞性身段的运用,对舞台时空的无缝衔接,以及对传统曲剧唱腔的时尚化微调,都让北京曲剧焕发出新鲜的色彩。而主创们并没有抛弃剧种自身的特质,尤其是在音乐和唱腔的处理上继承传统并给予创新。比如:由【撞金钟】的曲牌开场与结束,首尾呼应贯穿全剧;纸人们的唱腔则采用了民间曲调“骷髅叹”,而结尾处“我”倾泻而出的“花样红”唱段则成为全剧的点睛之笔,将我的悲剧命运与“笑”扭结在一起,更添苍凉。剧中,大量朗朗上口、幽默诙谐的民间小曲、小调,恰如其分地分布于角色塑造上,使得这个最容易陷入“话剧加唱”的剧种,在表现现代题材上丝毫没有话剧的痕迹,相反通过重复和变奏尽显戏曲音乐性的魅力。
由年轻人创作的这部《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是北京曲剧的一次突破——它忠实原著又加以创造,将老舍对北京人的深情转化于戏剧舞台,并让北京曲剧这一剧种在小剧场的空间内余音绕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