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弥:书写“人”的丰富与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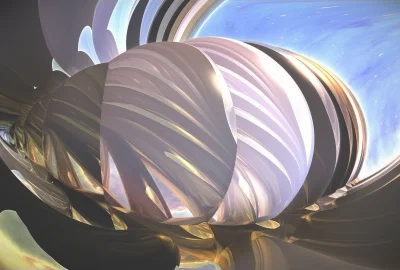
叶弥的长篇小说《不老》既可作为《风流图卷》的续篇,也可独立来读。事实上,当年叶弥在乡间生活写作《风流图卷》时,便有了这下一部的构思,她直言两者之同在于“风流”二字。在《风流图卷》里,吴郭城一众风流人物滋养了少女时代的孔燕妮,让她见识了与“传统”和“庸常”不同的生活,长大后的她自然而然地将情感当作了生活的核心。在《不老》里,孔燕妮等候狱中男友张风毅三年,其间则谈了三场恋爱,可谓一部“风流”的“情感史”。
为“情”设置绝妙的“容器”
熟悉叶弥的读者都知道,在她笔下,“风流”非“下流”,“用情”非“滥情”,整部《风流图卷》便是对“风流”这一词汇的祛魅。拂去尘灰,还其天真诚挚本相,为孔燕妮涤荡出了一个清澈坦荡的情感语境,让她能够心无旁骛地展开一场场爱情之旅。35岁的她看上去年轻、无畏、充满活力,就像书名所示,有了“爱”,所以“不老”。
【资料图】小说写“情”并不出奇,或者说,小说的天职便是写“情”。但众所周知,中国20世纪以来的小说写“情”负载累累,使其承担的内涵往往逾越了情之本义,这让现代中国人的情感面目模糊、疑窦丛生。在这方面,叶弥堪称“逆行者”。《不老》中的“情”相当纯粹,就是男女之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当然,现代情感之有别于杜丽娘、柳梦梅的是本能欲望的自然流露,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恋慕,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的心疼,用孔燕妮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对方“焐热”。
你可能会说,写“情”也没什么了不起嘛,的确,单单写“情”也撑不起一部长篇。《不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情”设置了一个绝妙的“容器”,让它在别开生面的结构和丰沛滋润的叙事肌理中尘埃落定。小说以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短暂日子为时间轴,展开了中国社会大转型即将到来之时的众生相。各种在对未来的猜想中展开的激进或保守的思想和行为纷纷出笼:或如喜欢谈时事的杜克成了“牺牲品”,或如美国人温德好旗帜鲜明地反美反尼克松,或如前诗人麻春雷悄悄集资办厂,或如心灵手巧的秧花在刺绣中找到了致富事业,就连远离尘嚣的青云岛也风云激荡起来。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不平凡的年份,是“前夜的涌动”。
与此同时,小说又从这一年里截取出了一个短时段,即离张风毅出狱仅有的二十五天,不足一个月。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孔燕妮与俞华南相爱了。两个人携带着各自的“情感前史”和“观念前史”,在猜测、龃龉、冲突、争吵中逐渐走近。“前夜”不断地向前奔腾,张风毅的出狱又在“倒计时”中一天天迫近——藉此,叶弥构建起了一个有弹性、有动感的叙事结构,用它容纳着时代景观与个人命运。宏观/微观、情感/政治、出世/入世、高贵/粗鄙等种种不同质地的景象在此交糅,构成了一曲宏伟明丽的“二重奏”。
为什么书写“爱的诗学”
关于《不老》的“爱的诗学”,李德南等论者已明确指认过。孔燕妮不屈不挠地追求爱,这种反传统的特质使得她难以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所容,她所到之处均有“看客”和流言蜚语,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她爱的愿望与能力,情路的趔趄坎坷也没有打乱她稳定的节奏,这是一个内心圆融自洽因而无法被伤害的女人。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张风毅在小说中从未露面但其影响力无所不在,俞华南在某种程度上又替代了张风毅,让读者感到孔燕妮对这个人的爱是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延续或强化。因为这两位男性虽性格迥异,精神面貌却极为相似,都敏感、多思、有激情。他们互为镜像,以“缺席/在场”的互补共同构成了孔燕妮最珍视的情感生活。
更进一步说,他们三个是同类,都是以精神为食粮的脱俗之人。我甚至倾向于这么理解:叶弥之所以安排俞华南从北京来吴郭调研,毋宁说是在为她欣赏喜爱的孔燕妮女士安排一个同路人。在所有人都在为未来激动或恐惧时,她却执着地深陷于恋爱,“与这个暗流涌动的时代毫无共同之处”。她的激进、行动及其与这个世界算的“进账/付账/平账”只关乎精神而无涉于物质。俞华南也并非日常琐碎之人,他用忙碌的调研和思考来消解“心里的黑暗和紧张”,修复情感记忆的深度创伤。这两个“古怪”的人都不为世人所理解,彼此却一见钟情,像小孩儿一样互留纸条,互相牵挂,见面时少不了嗔责,分开了又拼命想在一起。叶弥为他们设置了纯真有趣的“奇遇”,像是在表明,她就是要为这个被世人诟病的“坏女人”撑起一把“保护伞”,让她永不孤单,永远翱翔,永远葆有内心的自由和明净。
为高远清朗的精神主体建造“理想国”
这样说可能有过度阐释的嫌疑,可我确乎有以上这些强烈的感觉。喜欢叶弥的读者朋友可能和我一样,都被她笔下别样的美感和力量所感染,那种带着饱满的劲儿挣脱现实桎梏的强力,在平淡如水的生活表面留下了深深的辙印。叶弥曾说过,她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对现实的不满。因此,她不可能对着现实“照猫画虎”,而是要拔地而起去建造一个“理想国”。在那个国度里,合格的公民就应该是孔燕妮、张风毅、俞华南、老隐这样的“精神贵族”,至于像王来恩那样的小人,像谢燕兵、潘小根那样的庸人,统统不能进入“理想国”。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叶弥小说中的人与事仿佛与日常相“隔”而自带雍容高蹈的诗性气度。
说起来,某种生活之所以让人失望,是因为人们许多时候只能匍匐在泥地里或以在其中打滚儿为乐。在这样的语境中,叶弥竟然还在执拗地想象和书写高远清朗的精神主体,这真是让人震动。要我说,《不老》表面写的是“爱”、是“情”,内里依然是叶弥一以贯之的追索路径,就是去发掘、书写真正的“人”。什么是真正的“人”?就是具有情感和精神上的丰富性与无限性的人,他们天然地与鸡零狗碎、蝇营狗苟绝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过这样的形象,比如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准研究生,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张洁《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叶弥显然有志于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系列,他们不仅勇敢,而且有趣,自个儿就是自个儿的主心骨。就拿孔燕妮来说吧,她既勇于折腾,也不惮于受伤;既对弱者心怀怜惜,也对强者毫不畏惧;既热爱自由,也予人以自由;既喜欢谈恋爱,也不乏独立思考。她最终选择白鹭村是一种心地光明的入世,这朵在《风流图卷》中被老和尚所叹的“无根之花”在《不老》中长出了根。
我感觉,叶弥应该还会有一部以孔燕妮为主人公的作品。她不会把她留在“前夜”里,而会让她在“黎明”中再精彩绝伦地活一回,让读者们把她丰富多元的人生和爱情都欢欢喜喜地照单全收,那该有多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