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头条:如果穿越回《世说新语》 你以为你会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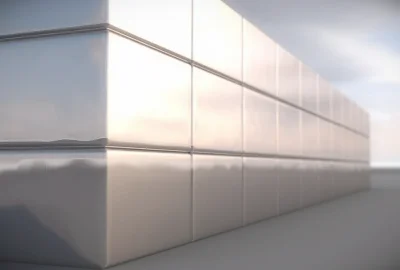
(资料图)
嘉宾:刘勃 文史学者
贾骄阳 中国社科院博士
文史作家刘勃解读《世说新语》,以《世说新语》文本为基础,参照《晋书》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精准考据,将魏晋时期的诸多名士放进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并展开多重线索的想象与推理,以更多元的视角诠释魏晋时期的风流与苍凉。
中国文人心向往之但达不到的梦
贾骄阳:《世说新语》是历代文人都极其喜欢的一部作品,辛弃疾的词、《红楼梦》里都出现过好多《世说新语》的典故。为什么中国文人会喜欢?
刘勃:因为《世说新语》是他们心向往之但达不到的梦。魏晋时期特别特殊,给名士们搭建了各方面保障都特别好的平台。魏晋以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在古代文明里比较而言是很强的,但《世说新语》这个时代又是阶层流动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弱的时期。所以那时候的名士们会有特殊的安全感。人活得有安全感,姿态就会比较舒展。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很“卷“,为什么“卷”?因为缺少安全感,害怕不参与到残酷的竞争中,就可能会更快被淘汰掉。当你安全感足够的时候你就不卷,那种特殊的舒展感是后世文人很想要又很难达到的。
但是,这背后有一种很残酷的东西。名士们活得舒展,实际上对于社会另外一些人来说,是一个挺不幸的事实。《世说新语》把最舒展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看了,更痛苦的那一面相对而言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贾骄阳:我在读您这本《世说俗谈》之前,真没有注意到《世说新语》背后的残酷或者是比较冷峻的那一面,这是不太被人关注的。
刘勃:一方面,我正是被《世说新语》里的舒展感所吸引,另一方面《世说新语》所遮蔽的那些残酷的东西,我希望把它呈现出来。对高度紧张对立的两面,我同时都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写的时候我会想要找一个撕裂感。撕裂,是我对《世说新语》和孕育《世说新语》那个时代最强烈的感受。
我会用我能想到的最刻薄的言辞,讥讽文人身上的臭毛病,可是我又是多么爱这些臭毛病啊。当我找到这样一种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感觉的时候,我的写作冲动就来了。非学术的随笔与学术书是不同的,肯定要少掉很多东西,但有时候可以多一点东西。对我来说,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情绪。既充满情绪,又能把情绪给收着,有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大概就合适了。
贾骄阳:《世说新语》里面的人物,很多现在看光鲜四溢而且引人入胜,大家会为之倾慕,但读过刘勃老师这本书,会发现代入不同视角有不一样的感受。
刘勃:我的书谈不上什么新发现。毕竟魏晋史研究是非常成熟的学科,高水平的前辈学者也太多,像田余庆先生的著作把很多问题都写透了。我顶多是在老先生重大发现的基础上,关注一些他们不会花工夫写的东西,这正好是我可以用力的地方。正因为我比较平庸,我和很多普通人的内心感受可能会有更多相通之处。
比如著名的“雪夜访戴”故事——某日见天降瑞雪,王子猷兴致大发去找好友,但舟至好友家门却不入,兴致而来兴尽而回。我有时上课会跟学生互动:假如穿越回去你会是谁?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残酷的。就像现代人不太可能下一世投胎成王思聪,大多数人穿越回去更有可能是厨子或者船夫。这样感同身受起来就会完全不一样。但我也不希望因为想到这一点就丧失对王子猷行为的欣赏,那种行为仍然是很美的。世界就是这么复杂。
给受束缚较多的人,展示另外一种活法
刘勃:谢灵运写过一篇赋,描述自己家的庄园,有几十平方公里这么大,庄园里有多少座山,山上有什么样的树,有多少条河、多少湖泊,里面有多少鱼。罗列完之后说,人何必一定要当官呢,像我这样过过苦日子不也挺好的吗?他还真不是在“凡尔赛”,他们社会位面就是这样的。
贾骄阳:所以魏晋时期像陶渊明这种文人太少见了,没有进入《世说新语》的可能性,大部分还是像谢灵运这样的状态。
刘勃:范(子烨)老师不是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世说新语》里为什么没有陶渊明。
贾骄阳:从陶渊明的地位来说,《世说新语》的作者不会把他列为应该记下来的人物,包括他的作品,并不比谢灵运的诗歌更为人称赞。这是《世说新语》里能看出来的东西。
《世说新语》主要是对魏晋时期,也包括东汉一些人物的记载。跨越这么多年,您觉得现代人读《世说新语》会有什么意义?
刘勃:意义这个话题不好说。我们活在受束缚比较多的状态下,《世说新语》给你精神上的放松,给你展示另外一种活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意义。
我从小爱读《世说新语》,小时候很大程度是被滤镜骗到了——《世说新语》诱导你向往那种生活。可是后来你才明白你不是琅琊王氏、不是陈郡谢氏,你要面对很多很残酷的现实、受到更多束缚。我们比不了他们的社会位面,比不了那种不把别人感受当回事、可以肆意折腾普通人的“人上人”状态。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物质方面,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比那个时候的膏粱子弟差。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古代人无法想象的物质资源,我们作为现在很普通的人,我们能享受的很多东西就比他们还要好。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穷人,如果穿越回去和古代社会的穷人交流,我们的社会位面可能是相似的,但是交流起来反而会很困难。他们的生活是被压榨得一点闲暇、一点余裕都没有的,而人内心很多细腻感受是需要物质性的东西来滋养的,这是古代穷人没有的。现代人就算自我认知还是穷人,但还是享受到了不少物质、精神上文明的滋养,这样现代意义上的穷人,内心一样可以细腻起来,感受一样可以丰富起来,大家仍然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文化产品。从这个层面讲,我们反而和古代上层阶级有共通的语言。当我们抛弃掉特别有阶级感的东西,只从人内心细腻微妙的地方去品味,反而可以和《世说新语》当中的名士感到很多相通。
现在回头看,才意识到最近这40年是特别伟大的时代,人有选择的多样性。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你如果做一个乖孩子,从小好好读书,会得到很好的回报。教育的回报如此之高,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或者你是特别叛逆的孩子,你就是不守规矩要到外面乱闯,也有无穷的机遇。哪怕像我这样,性格又别扭脑子又笨,但有一个爱好。你会发现你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面,好像这么多年下来得到的回报,也至少超过了我自己的心理预期。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希望现在的孩子们将来面对的世界,可以更广阔吧。
打动人的是时代里的困境,以及面对困境的挣扎
贾骄阳:《世说新语》里面您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位?
刘勃:喜欢的人很多,真的很难说具体喜欢哪一位。
我如果决定要写一个人物,他身上肯定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但是打动我不一定是因为喜欢他。《世说新语》呈现给我们的是这个人特别光亮迷人的一面,但当我们把当时更具体的历史情境还原出来之后,又能看到更残酷更血腥的一面。打动我的是人在时代里的困境,以及面对困境的挣扎。
在《世说新语》中有一个并不是很显眼的人物赵至,他算是嵇康的粉丝。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是什么人设——我不想当官可是人家非要逼着我当官,我好痛苦。赵至这个人虽然也是嵇康的朋友,也和那个圈子有接触,但他的人生不一样。他的爱好可能跟现在很多人的需求更相似——我想当官可是我没有机会。他是士家出身,这属于当时很特殊的人群,这样家族的孩子注定是要当兵的,不要说和高门大姓沟通,和一般平民通婚都很少。
因为到战场上肯定会变成炮灰,所以赵至无论如何都要摆脱自己的士家身份。可是如果直接逃亡,又会连累自己的父母。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又不敢这样做。所以他假装发疯用火烧自己,像一点不知道疼的样子。上面的人一看这个人已经疯了,不适合当士兵,所以他成了人口统计中因为没有实用价值不被统计的人,这样他才得以逃脱命运。
之后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当官,隐姓埋名跑到东北很荒凉的地方终于当上官了。后来他回家见到了他的父亲,当时他母亲已经去世了,由于母亲一直期待他能当官,父亲害怕他不继续努力当官于是没有把母亲的死讯告诉他,叫他赶紧走。所以等他终于又到首都汇报工作时,才知道自己母亲死了,他痛哭吐血,自己也死了。
这个人其实跟《世说新语》里边很多名士是有非常鲜明对照的。当时写到他我比较激动,现在讲他我也比较激动,你们应该能感受到。但换一个角度讲,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也是一个士家子弟,我身边有一个赵至这样的人,我会不会很喜欢这个朋友?恐怕不一定。因为他特别轴特别狠,一个能够那样虐待自己的人出现在你身边,你很可能是怕的,你可能是要和他保持距离的。
正是因为如此,阅读当中遇到这样一个形象,对我来说太震撼了。这也就是文学的意义,距离的拉开可以让你理解更多人。当你面对身边人的时候,假设你与他保持距离的时候,你是不是对他有多一点体谅、多一点宽容?这是《世说新语》里一处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贾骄阳:《世说新语》是名作,解读它的作品浩如烟海,此类作品中您觉得《世说俗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刘勃:特点就是我比较笨。譬如我刚刚讲到的赵至的故事,唐长孺先生首先注意到这一条并写了考证的论文。唐长孺先生的论文是有阅读门槛的,像我这种更啰唆、情绪更多的叙述,有时效果可能会呈现得更直接。
笨人下笨工夫,可能更易与大多数人共鸣
贾骄阳:《世说新语》是我以前的研究方向,它非常好看,有些篇章直通人的灵魂,可笑、可气。但《世说新语》确实非常有难度,因为书里人物很多,彼此关系繁杂,里面使用的语言也有很多方言甚至包括当时的古语。所以是很有门槛的一本书,你想真正看进去是很难的。
刘勃:《世说新语》难读,我自己也特别有体会,主要是书里人物、人名太多。当然很多老先生已经把最艰巨的工作做了——一个人名第一次出现时下面会有注释,注里会提示后面书里会出现这个人物的其他称谓;有的老先生还整理过人物表,表里会告诉你这个人在《世说新语》哪一门哪一则里出现过。
对于特别优秀的大脑来说,看过老先生的说明,就能够把书整个串起来。但我这种比较笨的读者,可能有这么一个困境——虽然前面看过注释了,看到后面恍惚记得前面老先生有过这么一个说明,但老先生怎么说的记不清了,书就得往回翻。我想我面对的困境应该和很多读者是一样的。所以我首先得给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花工夫去做一系列的表格,把很多零散的东西串起来,再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这样也许能够更加适合一般读者的体验。有时候笨人下笨工夫,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共鸣反而更容易。要说本书有点特色就是这个。
贾骄阳:我读过很多通俗性解读《世说新语》的著作,从来没有一本书像《世说俗谈》这样,能如此清晰地将一个人的条目按照一个人的发展、时间顺序、成长、史事发展顺序来重新安排,这个工作是很多学者内心中很清晰,但普通读者不太明白的。由于《世说新语》是分36门来架构,根本不是按时间顺序,所以你看着看着比如说桓温就出来了,可能这是45岁的桓温,这是20岁的桓温,这是晚年的桓温。刘勃老师是拿条线把人物串起来了。
刘勃:《世说新语》里写到一个人不会强调他的年纪。还有一个对于现在读者来说可能很不舒服的习惯,书里常会出现拿这个人后来的职务、称号来称呼早年的他。如果今天电视剧这么做都会被笑。比如说,“竹林七贤”里的山涛,有次某人想跟司马懿推荐山涛,说山涛可以和你们家司马师、司马昭一起创业,原文居然称呼司马师、司马昭“景、文”,俩人死后的谥号居然出现在直接引语里,《世说新语》里有很多这种现象。
解决这种问题,把时间线重新捋一遍还是很有帮助的。怎么捋?一是政治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他在史书中可能有传记,传记本身就会提供时间线。另外一些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可能在正史里没有传记,但老先生研究作品集工夫下得都不得了,他们给很多重要作家都编过年谱,基本台阶搭好了。我做的就是一个通俗化的工作,把《世说新语》里的条目按照老先生已经做的年谱,把材料重新编排一遍,再转化为叙事。如果你要了解《世说新语》中的人物,读这书门槛比原来要低不少。
贾骄阳:还有,读《世说新语》,你得对魏晋时期那段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也好、人物之间关系也好,前情和渊源有一定了解,有些条目才能读懂。比如王述为什么称桓温为“老兵”?类似这种称谓,可以把相关的社会背景这些东西非常传神地点出来——这是因为当时人对于士兵是很歧视的状态。
刘勃:《世说新语》里确实有很强烈的对军人的歧视。这是当时文化很尴尬的特点,一方面维持国家秩序不可能不要军队,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舆论风气对于士兵很不尊重。我们如果不知不觉拿现在的气氛去读古代的状态,确实容易理解不了,我想加一点说明。
适度使用大白话,算是对《世说新语》的一种古今呼应
贾骄阳:另外这本书的名字非常有趣,《世说新语》给人历来印象是说雅致的名士,我们今天叫《世说俗谈》,书名里的“俗谈”您怎么考量?“俗”这个字怎么解读?
刘勃:我觉得还原背景本身就是很俗的工作。当人物背景更多呈现出来之后,原来那种雅的滤镜一定程度就被破坏掉了。我这个写法本身也比较俗,会有很多的大白话。但我同时又觉得使用大白话算是对《世说新语》的一种古今呼应。
贾骄阳:《世说新语》里本身就有很多口语,甚至还有很多粗口。
刘勃:它本身是一个有很多口语的书。现在不少读者对口语相当地反感,一旦使用了口语,文章好像就不够高级。但是,当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文学传统,实际上你会发现最伟大的典籍,除了中学语文教育中提供的那些高端解释之外,经典中也充满了口语。像《论语》里孔子和学生的对话状态,可能很多就像是贾老师和学生说话一样。
贾骄阳:“野哉由也”,太野蛮了。
刘勃:司马迁《史记》里面也有大量的口语。他做了一个工作,把记录上古历史的《尚书》里佶屈聱牙的语言,改写成秦汉时期比较口语的描述。还有为了塑造一些劳苦大众的形象,司马迁记录他们说话,直接就是口语。事实上,正是口语在不断地给文化传统、文学传统提供活力。一方面是雅致的语言,是传承,是相对稳定的一面。另一方面,口语又不断地在提供新鲜的血液。经典的语言就是雅和俗两者完美融合起来,这才是文学的活力所在。
其实,我中学时候是特别喜欢用书面语,而且翻译腔很重的人。三十年前的社会氛围,谈起中国文化,国人普遍是有自卑感的。因为有西方滤镜,那会儿我跟朋友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大家一张嘴都是西方后现代文学、实验文学,像我这种同时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在那时候就像有人生污点一样,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这个。
因为有西方滤镜,写东西的时候你的文字有浓重翻译腔,似乎高级感就来了。我中学写东西,翻译腔特别重,但后来我也开始上网了,网络语言、日常生活语言都在混着用。
当时也有我特别敬佩的前辈跟我说:“写文章要少用口语、网络语,因为这是特别容易过时的东西,不稳定。我们现在把十几年前网络流行语词典拿出来,你看看那些都是什么东西。”流行的反而是更容易过时的。如果多用流行语意味着文章会很“短命”,几十年后、十几年后人家就看不懂了。那段时间我觉得这种说法特别有道理,所以一度又减少了口语的使用。
但后来我想这不对,还是要用口语。为什么?因为口语或流行语,最容易展示特定的氛围感。我不想牺牲这种氛围感。至于说生命力的问题,如果我的文章没有价值,过了十几年就过时了,文章中的口语也过时了,反正都过时了,过时就过时吧。如果我的文章有价值,几十年后还有人看,看的人就会去琢磨这个口语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口语是我生活的年代流行的词,几十年后居然有人在琢磨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给我们自己的青春时代多留下来一点印迹吗?
所以,我文章里的口语将来命运会怎么样,听天由命吧。就好像《世说新语》里边,如果没有“阿堵物”“宁馨儿”,那还是《世说新语》吗?《世说新语》里最口语的部分可能是现在学者研究最来劲的部分。所以对于口语,想用就用吧,这也是我“俗”的部分。
贾骄阳:我读的过程中,有时候像在看单口相声的感觉,某一些解读让人哑然失笑。
刘勃:一方面,表述是俗的;另一方面,希望没有用俗伤害《世说新语》本身的精致、本身的美。
有不少篇章写得还是很感伤的,泪和笑交织在一起。搞笑成分重一点,再猛地切换到伤感、流泪、痛苦的部分,也许反而会更加有冲击力,这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
质而实绮,找到雅俗之间最为恰切的位置
贾骄阳:比如写到祖逖和刘琨少年的情境,之后波澜起伏的人生交织。书中的最后一个场景是刘琨吹着笛子,在一片月下。书中这样写完全是写小说的笔法了。
刘勃:那一条也是非常有趣,现在通行版本《世说新语》已经没有这条内容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世说新语》是不全的,要通过其他书的引用,才知道《世说》里曾经还有些什么。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情况,写《晋书》的唐代史官文人气比较重,把这一段写到了《晋书》。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则去掉了,他觉得那段太浪漫、太传奇了。很多时候,材料就那么点,写还是不写,把这段材料放在文章的什么位置,其实很能看得出作者是什么样的“形象”。
我是知网深度用户,每天泡在知网的时间特别多,下载各种论文看,会有一种感受:很多东西,咱们接受过中学教育之后知道ABC,前辈的学者已经研究到了XYZ。很多年轻学者为了发论文、拿项目、搞创新,在琢磨再搞一个新字母出来。但可能大多数读者更需要的是DEF。任何时候绝对要尊重学术界的成果,但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往那个圈子里挤,我好好把DEF讲得大差不差,这个工作也算是有点意义。
贾骄阳:真的是这样。第一是这个作品一般很容易是阳春白雪,没有解决阅读的问题。第二是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戏说,完全用现代的语言,没有史实的推测或研究,这样的文章有点像用微博段子写成的东西。这本书除了有趣、俗谈以外,刘勃老师达到了中间非常平衡、非常漂亮的状态。后世评价陶渊明的诗有一句话叫“质而实绮”,说它的诗很质朴,但其实非常绚烂。跟这个有点相似,可以看出刘勃老师不是在这儿完全编创或者自己开脑洞,而是背后有史实和史籍的支撑。这本书不是戏说,为广大读者找到雅和俗最为恰切的位置。
刘勃:这是我会思考的点。尤其是唐以前留下来的文献是非常有限的,有很多东西就是动人的片断,相关很多细节是没有文献留存下来的,这时候肯定会脑补。脑补是因为共情,你读到这一段文字,心里被触动了。要看你补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写到脑补的东西会有明显的提示,我会写“也许”会怎么,或者同时提供几种不同的“也许”,因为这是不确定的。或者我会写他“不知道什么”——当事人是不知道的,我们作为后来者确实有后见之明,有那么多学者提供那么丰富的研究资料,当事人不知道的东西可以以这种方式记录下来。我肯定守着一个底线,不会虚构人的言论,也不会虚构人的心理活动。

